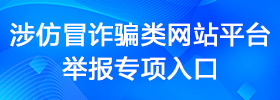郑安国:故乡,及其他
故乡,及其他
作者:郑安国
一
无论怎样,我都是很愿意回到隐水的。
尽管那里曾经葱郁的青山变得光秃,除了满目的野荆和裸露的山体,已听不见猫头鹰的叫声,看不见野猪和山兔箭一样射过清清涧峡和枞树林。那些从前牧歌悠扬的美丽阡陌和田垅,此时被荒草弥漫,村庄上空斜着几缕炊烟,这偌大的村落,除了几声犬吠和鸡啼,只有人语寥寥。从前涧边山顶高旷悠扬的山歌呢?它们都消失了么?
父兄们哪里去了?童年伙伴哪里去了?姊妹们哪里去了?
踏着微现着白霜的山路,我感到一种凄清和落寞,这条路不知走过多少代人了,它依然仄狭不平。多少年来,只有游子循着这条脐带来寻自己的根,如今父老乡亲却沿着它走向山外,仿佛雁阵横过黑土地,有些永远不再返回,有些成为村庄的另一种候鸟,飞得憔悴飞得沉重。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的父老乡亲宁愿在异乡的屋檐下仰望明月或聆听淅沥的雨声,尝那份背乡离井的酸楚,也不愿回到自己的故乡。
我无言。但我深知,生活永远是美好的。
我的父老乡亲世代劳作在田园,无怨无悔,忍辱负重,心底宽厚地面对世事,但他们有他们的尊严和对世道人心的认知,他们把困惑和希冀埋在心里,艰难地写着他们的人生。
许多代人已老死在逼仄的田园里,许多的旱涝和灾祸都挺过去了,但如今兄弟姐妹却候鸟一样飞离故土,漂泊在陌生的异乡,他们是存着一份向往,也怀着一份无奈吧。
许多的父兄和叔婶都死去了,山坡上的新坟和旧坟在寒夜里闪动着磷火,他们奉献了一生。生前吃苦太多,死后却很冷清,他们的后人都到山外去谋生去了,已差不多忘了埋在土里的亲人,就像忘了遗落在责任地里的红苕和花生。
许多的姐妹都已嫁了人,她们都用不太美丽却贤惠的青春在很远的村村落落劳作,生养后代;甚至她们在很大的城市里花枝招展,在花花世界里尽情任性。如今她们已消失在异乡人海,我已再见不到她们的面容。
我无法追回这逝去的一切。
人不能安守清贫的时候,便学会流浪。村庄就像一部古旧的农书塞在山缝里,只有岁月的风在无声的翻弄。
我不知道这世代播种着汗水和泪水、收获了贫穷也收获了快乐的田园为什么被人离弃。田园,美丽且苍茫的田园啊,你到底怎么了?是你的泥土不再养人,还是你中秋的明月不再浑圆?是你的阡陌不再美丽,抑或是你的山歌和炊烟不再温馨?为什么没有了眷恋,为什么人要逃离你的庇护,宁愿去漂泊?
在寂静的月影里,我凝望着这依然美丽无言的村庄,想起它落着大雪时的动人景象和春花灼灼的晴日,想起童年的嬉戏和无忧,想起许多的人和事,我仿佛明白了人或许是应该离开故土的,只要心中装着,哪怕在天涯,也会感觉着它的存在和召唤。我和那些兄弟姐妹一样充当着游子,可是这脚下的田园永远以无言的美丽和亲情召唤着远方的灵魂。
人,譬如我的那些父老乡亲,他们只有一群敛翅栖息在故乡的候鸟。
二
人都是候鸟,终是有离开的。
只有一样是我无法与之孤隔开的,那就是大地。我一辈子都会在大地上行走,直到将来某一天,我走不动了为止。
少年的时候,不知愁滋味,整天只有无边际的幻想和憧憬,像天空里变幻不定的云彩一样,我没有认同一样将来的归宿。大地对于我来说是平坦无边的,任我游移和骋驰。面对一个无边的大地,一个孩子的内心里充满了激动和好奇。我一个人在收获过的麦田里过夜,在麦垛上呼吸着清凉的夜风,昂头注视着满天的星星,在黑暗里听到大地的秘语和星星的歌声。夜风传来了远处村庄的动静,稀稀落落的犬吠和人声已经遥无可辨。树叶在风里的呼啸已经成为夜语中最为宏大的动静,黑暗中,眼睛失去了观察了对像,我闻得到花香以及遍地麦茬的气息——散落于麦地之间的麦粒、野草、被踩死的蚂蚱和腐烂的蚯蚓,我却听见了花开的声音以及这些细微的变化,在被水浸泡和腐败时产生的细微的动静,有时候,可能自己听到的一切都只是一种幻听,就像在极静状态时,耳朵里会产生一种嗡嗡的轰鸣一样。幻听其实是一种心灵感触到的声音,有时候,在夜里,会听到自己心脏跳动的脉搏声,像潮水一样起起落落,各种神秘的液体管道贯通全身,它们日夜流动着。可是,我相信,在那一个夜晚,我听到的声音全是来自于真实世界的。大地在呼吸,不是么?这呼啸的风就是它澎湃的气流;大地在歌唱,远处近处的虫吟和树叶的婆娑、河水的波浪抚摸着堤岸、花朵在夜风中摇曳……声音来自于心动,这就是那宗著名的禅宗辩语“非幡动、亦非风动,乃是心动”,大地之心在动了,我的心也在动了,于是,我听到了大地之语、大地之歌。那一夜,我似乎成熟起来了,我听到了一个真实的世界之音。冥冥之中,仿佛有一个智者指示我,这就是大地——万物之母,一个能够产生无穷生命的大地的私语。我仿佛在黑暗中看到了自己的前生和来世,在大地的此端和彼极,有无数的声音在响起,连贯成海。
清晨,早起的我看见了一轮红红的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群山众壑为之动容,天空中布满了橙色的光辉。大地诞生了一颗新鲜的太阳,那连绵的晨风是不是它分娩时微微的呻吟?那一轮太阳像一枚鸡蛋黄一样,柔软无比,大地在某一处砉然开裂,从产门处娩出这一枚太阳。凝穆的大地,我听不见它深夜里的呻吟,清晨里的树伫立不动,万物肃静,在注目着万物之灵的诞生过程。
此时,大地静得只听得到自己的心跳,我的心跳在一次次地冲击着肺腑,血液像隐秘深处的河流澎湃激荡。大地在疲惫地喘息,清晨的微风拂过大地,雾气蒸腾,那是大地升起的汗水。河流在静静地流淌,田野上的树、草和花朵在欢呼,这种声音只藏纳于一种大音的背景之中,我看到空气流过大地形成的旋涡,风夹着轻尘扶摇而上,树叶、草和花朵在摇曳中微微颤栗。阳光轻轻踩过疲惫的大地,在它母亲的乳房和胸脯上踩着,大地欢愉地裂开一条条细缝,一种斫裂的脆响从地底下向上传递。大地富有弹性的肌肤将阳光向上弹起,光芒越过村庄和河流,直向远方。

三
普里什文在《大地的眼睛》说:“一切者听得见,一切者看得见。”“春天的光明、树叶从枝梢萌动的微响,小鸟啄破卵壳而出的第一声嫩啼……森林里的水滴,泥土里钻出来的昆虫在摩擦着翅膀。”“一片花瓣掉落在草地上,敲弯了另一棵草的腰。”“布谷鸟的声音像一些不连贯的音符,撞击着窗户边缘的冰凌,土地裂开了无数条缝隙。”他是一个大地细微的观察者和聆听者。经常在森林里出没的人都会有一种体会:那就是树叶生长的声音是清晰可闻的,一个无意坐在草地上的人会突然感觉屁股底下有什么东西向上刺痛他,起身一看,原来是刚破土而出的春笋。
树叶萌芽的时候,在一夜之间,所有的树叶都争先钻出坚硬的树皮,迅速地舒展开,那种积蓄已久的力量是惊人的,它们在发出一种持续的声音,这是一种次声波,它能够传播得更远,在方圆数百里的大地上,这种记号或者说是大地的暗语在传播着。在地底下,蠢蠢欲动的树根同样也在扩张着,膨大并继续延伸,向更深更远的地方探入。泥土胀裂的声音同样是次声波,是超出我们听域的秘语。大地在改变着,这些秘语在无声地传播向远方。在春天,收拾大地上意外生长出来的菌株,经如松蕈,在松林冈上细心地寻找,那些其貌不扬的家伙就混在掉落的枯松针底下。有经验的人会用耳去听这种动静,当它顶开地表的落叶和泥土的时候,会有一种细微的声音。春天的时候,收笋人在繁密的竹林里寻找恰在此时好冒出土的新笋。竹笋出土的势头很强劲,像动物一样迅速,一夜之间竟可以长高数尺,夜深人静的时候,听到竹林里一片砉砉的声响,那是竹笋在拔节。竹箨爆开时,发出一种脆响,像折竹之声,竹节吸过雨水后,极速膨胀伸长,声音哗然。所以,寻找竹笋不是件难事。有时候,砍下来的竹笋背在背篓里,还在长,身后一片竹箨迸裂的声音,竹林人说,瞧,竹笋成精了!山里的万物生长皆不徇定规,曲折成长,或快或慢。曾经听到一个山民说:他上山时曾经将一把砍刀忘记在某棵树下,再也无法找到了。后来,有个人伐倒一棵树,在树心里找到那把已经锈蚀的柴刀,树已经将它慢慢吞噬了,树吞刀的事情,应该不会是不动声色的,一定会有一番尺风雨的搏杀,最终,柔软的树“吃”掉了坚硬的钢刀。
在梅山峡的观音岩下,有许多人将折下的树枝倒插在岩缝的泥土里,让这些树枝“支撑”起岩石的重量。有些枝枝竟然长出根来,成为一棵异乎寻常的小树。这些树竟慢慢地向上曲折伸长,最终弯成触目惊心的造型,当地人称这些树为“撑腰树”。一些岩石被树撑下来了,坚硬的岩石竟也拗不过这些柔软的树枝。这其间一定也会有惊天动地的较量,能够将岩石撑裂的力量不容小视。可惜,我竟听不到这种惨烈的声音。
曾经认识一位老僧,他有一个癖好,就是在山里孤岩上打坐入定,我问他:僧有所闻?僧不语,等他睁开眼睛,他说,我是在和大地交谈,他听风语、树语、野草语、花语、岩石语……我奇讶:石能言乎?僧点头,能言,你且看,那遍山的草木能语乎,草木生于石上,故石也能语。我环视四周:岩上苍苔可人,岩缝中还有星星点点的野百合和骨碎补,在风中袅娜不已,《昙宗秘录》中说:“无一切语,无一切不可语,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石无一切语,其实石语一切,我们听到的是语,听不到的也是语,只不过那需要用心去领悟。佛说聆听诸相,有关心语为最,用心聆听,就是悟的过程。一棵树能生云,是奇迹么?非也,是因为云知道树不会挂碍自己,想想,倘若云知道一旦沾上了树就再也脱不掉时,那片云肯来冒这个险?同样,如果处处皆可闻语,那么,就是一种吵杂无序的噪音了。这么说下去,就有点玄了,打住。随眼皆风物,处处有禅音,这就是自然的物语了。
大地之秘语,是可闻,亦不可闻。
四
一场山火过后,山野一片狼藉,处处是烧成黑炭的树木残骸和动物尸体,地上是一层厚厚的炭灰。那一夜,山上风呼树骇,走兽奔突,惨叫声不绝于耳。大地在烈火的炙烤下坼裂涅槃,生命消失了,地底下的虫蜇也随之燔成灰烬。可是,过不了多久,这里又会长出茂盛的野草,新的树会从残根部萌生出来。再过数年,一切将恢复原样,又是一片草木峥嵘、繁花盛开、藤蔓罗地、飞禽走兽竟逐于此。
火是一种最冷酷的语,是大地最彻底的沐浴和更新。火语为何?火是一种极端的结束方式,是生命与非生命的一次大转变,想必,树木在火中一定会惨号惊呼,生命力旺盛的野草也难逃一劫,野草毕毕剥剥地燃烧,随火焰而舞,这是一种放达的哀歌,视死如生,就是野草的性格,树的身体在火中化为炭灰,这一定要忍受极大的痛苦。这种哀语孰能闻之?大地静默无声,虽然它同样也要承受着剧烈的疼痛。
诸般痛苦,只在一瞬间,生者亦痛矣,死者浑若睡。天地不仁乎?有时要作这样想:天地是不会特意去关照一个生命的生与死,天生地育,那是造化的本能。一切变化都是一种缘分,生是,死亦是。天语为震霆,地语为风。在三明万寿岩古人类活动遗址,我看到了三万年前的先人们在地穴里燔火的痕迹,他们留下了许多石器和动物的骨骸化石,这些已经消逝于时光长河里的镜像竟会在我的眼前一一幻出,茹毛饮血的时代,他们作为智慧的灵掌类动物之长,还处于鸿蒙未昧的时期,不会想太多的事情,他们只是为了果腹,才创造出了那么多工具来。他们用硬石来磨砺另一块硬石,在火星四溅之下,在空空的敲击声中完成了第一件工具的制造。他们不会留心那动听的石击声,不会为大地即将诞生人类而欢呼。大地在那一刻一定是欣喜若狂,毕竟,从此以后,万物有了主宰,万灵之灵即将诞生。
我注意到了,那是一些普通的鹅卵石,青色的和黄色的石锛、石斧、石刀是一种艰难的敲击的结果,这里头已经融入了人类早期的智慧。因此,它们看上去一点也不比我们现在的一切工具逊色,想想,如果让我们现代人不借用任何工具,仅凭一双手去制造这些石器,又有几人能够完成这样的任务呢?远古的声音已经消逝,远古的骨骼已经化为坚硬的石头,这个洞穴能与否?我伫立于洞中,听到的是洞外的风声树语,鸟语花香。可是我相信,这些石器一定记忆下了那段历史。考古学家从那些简单的石器造型上解读着三万年前的秘密。
春天过后,遍地的芦苇纷纷抽出或紫或灰的花序,像许多隐寓秘语的旗帜。大地生长出更多的花草树木,那些雀舌黄杨、木荷和青冈栎抽出红艳似花的新叶来,这分明是一种欢悦的语言,来自于大地深处的秘语。花开的时候,山野里有许多种鸟在鸣叫,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地之语已经幽微难辨了。我听得满耳的风声、树声、草声,听到水滴岩石的脆响,听到水流淙淙,大地开始新一轮的孕育期。就在此刻,我敲击着电脑键盘,听到的窗外树叶的呼啸,狂风骤起,那种隐隐的声音自远方传来,我在静静地聆听着、记录着。
上一篇: 德不孤,必有邻
下一篇: 李城外:“铁杆”金戈















 鄂公网安备 42122402000111号
鄂公网安备 42122402000111号